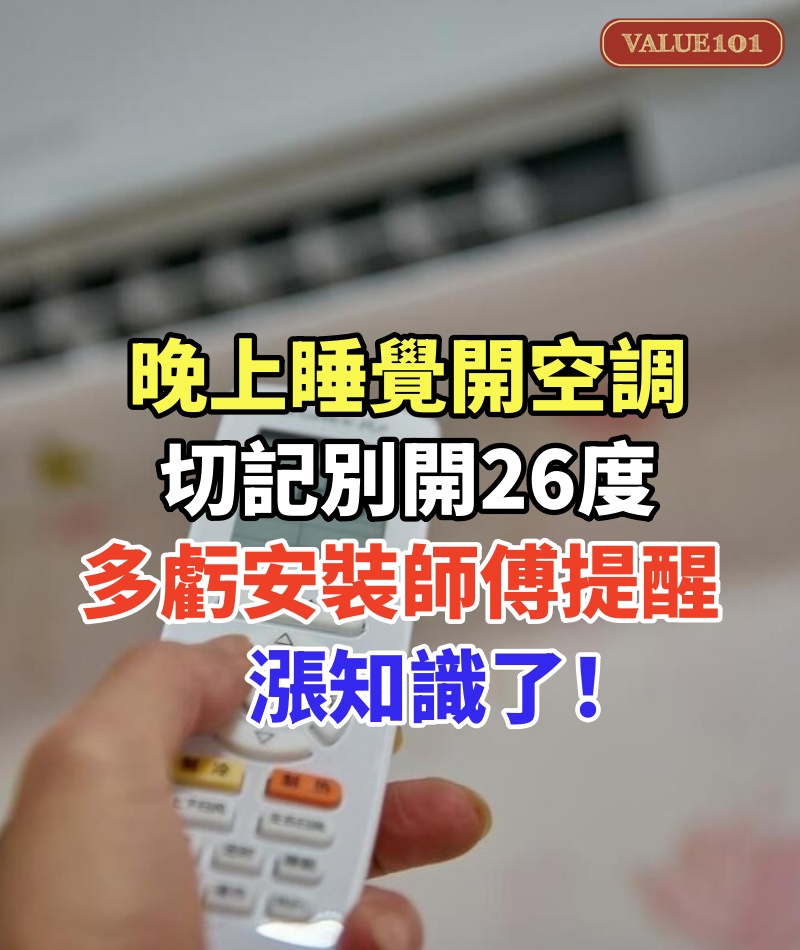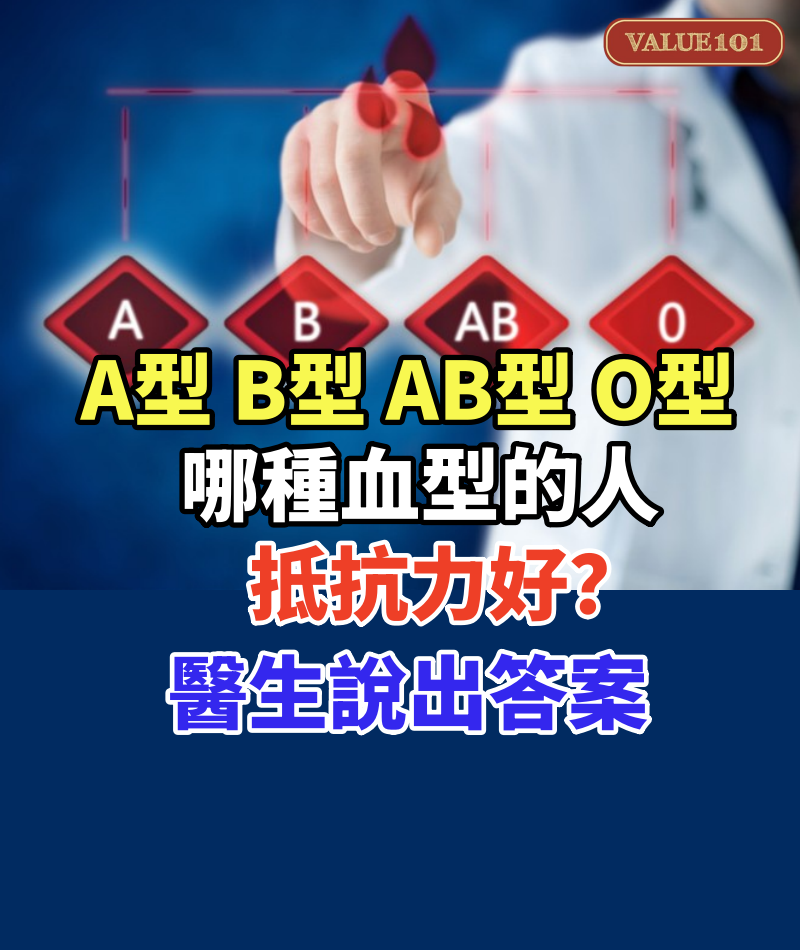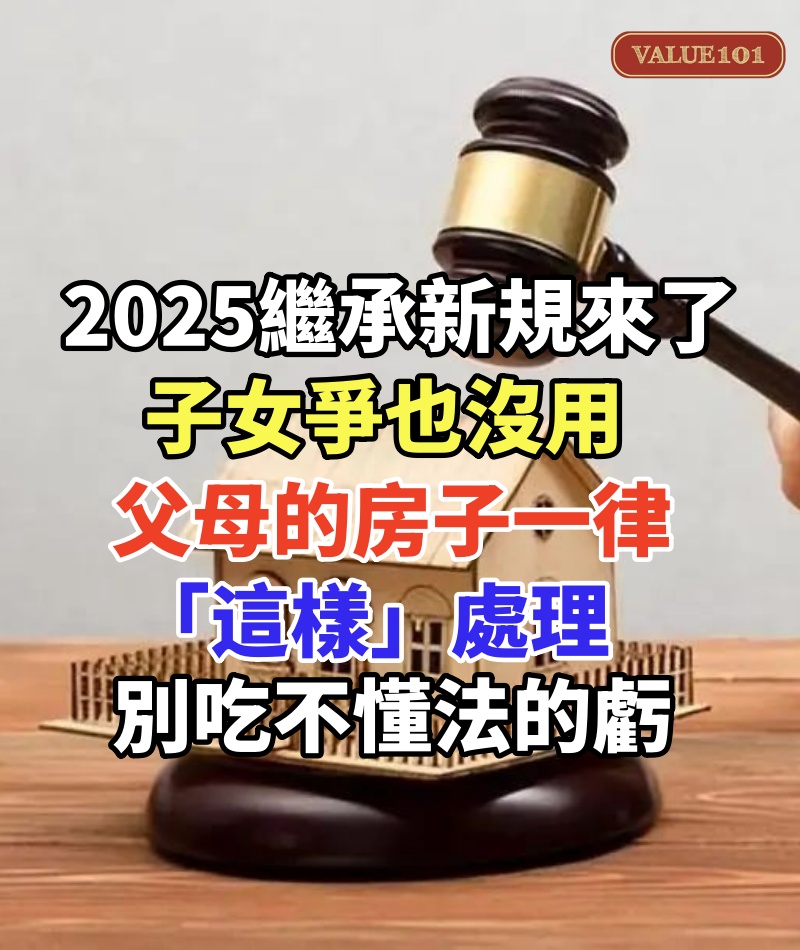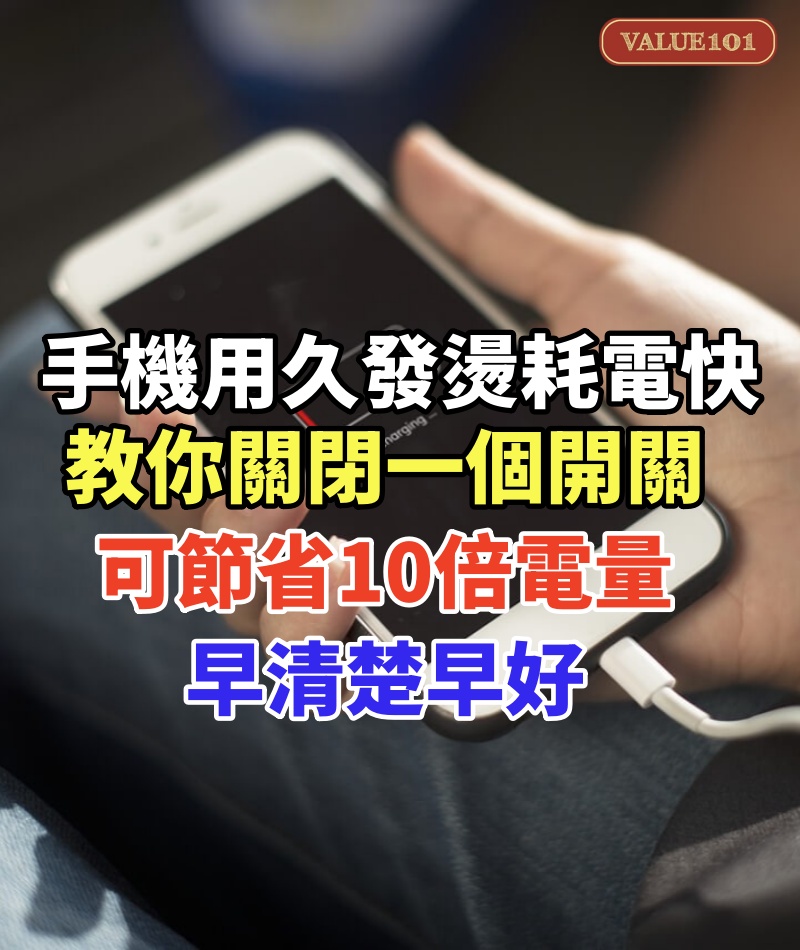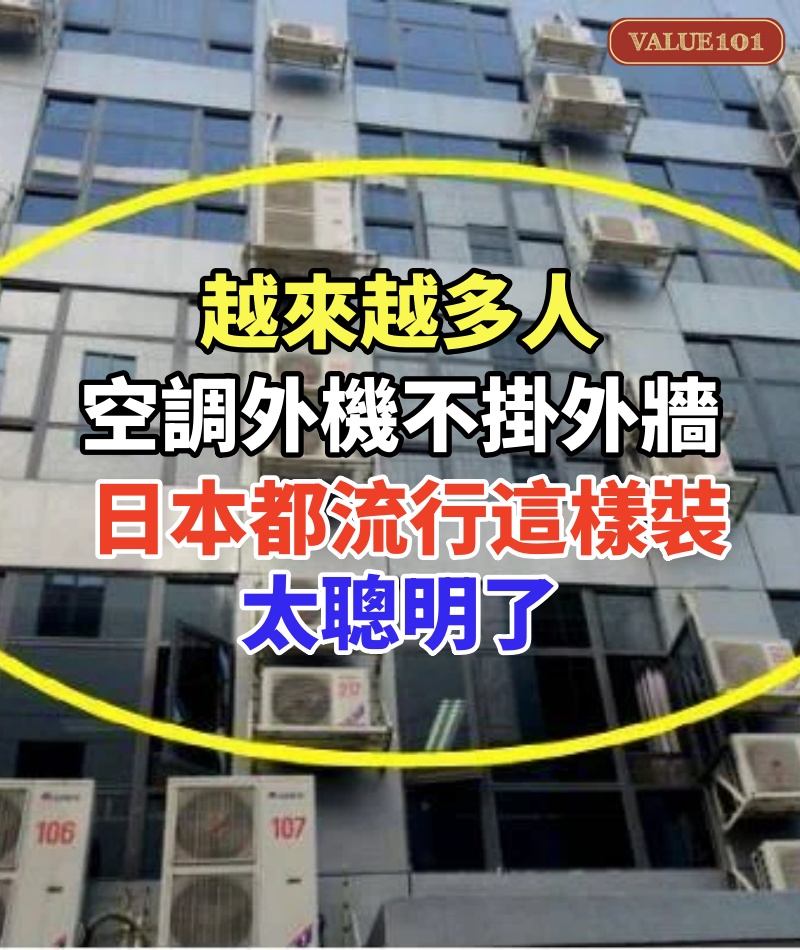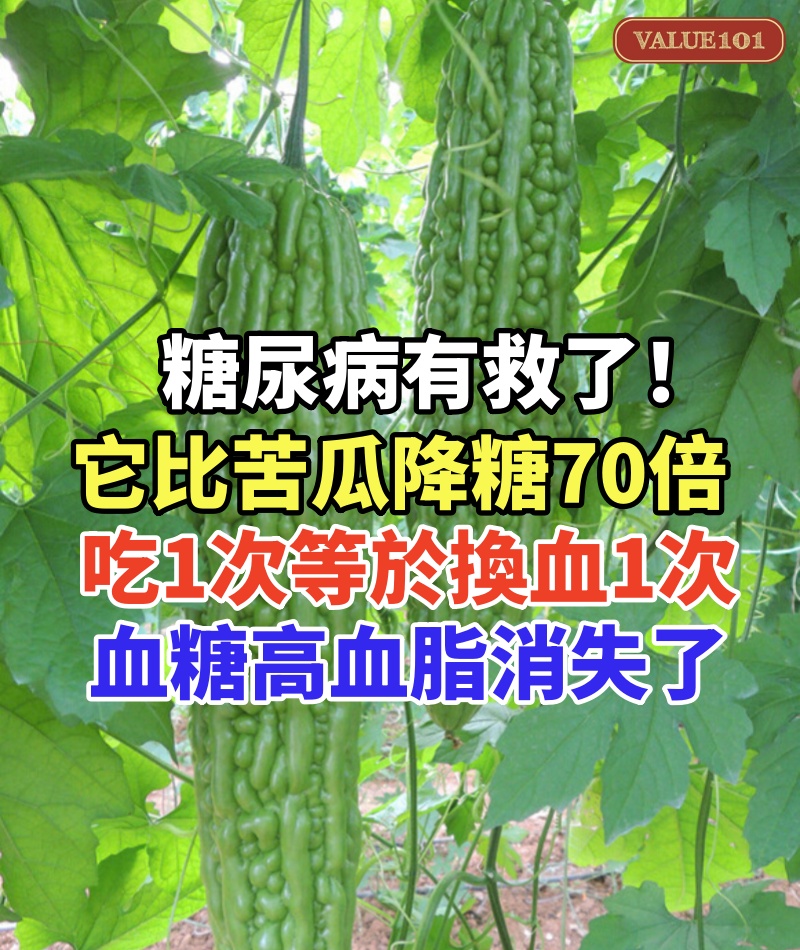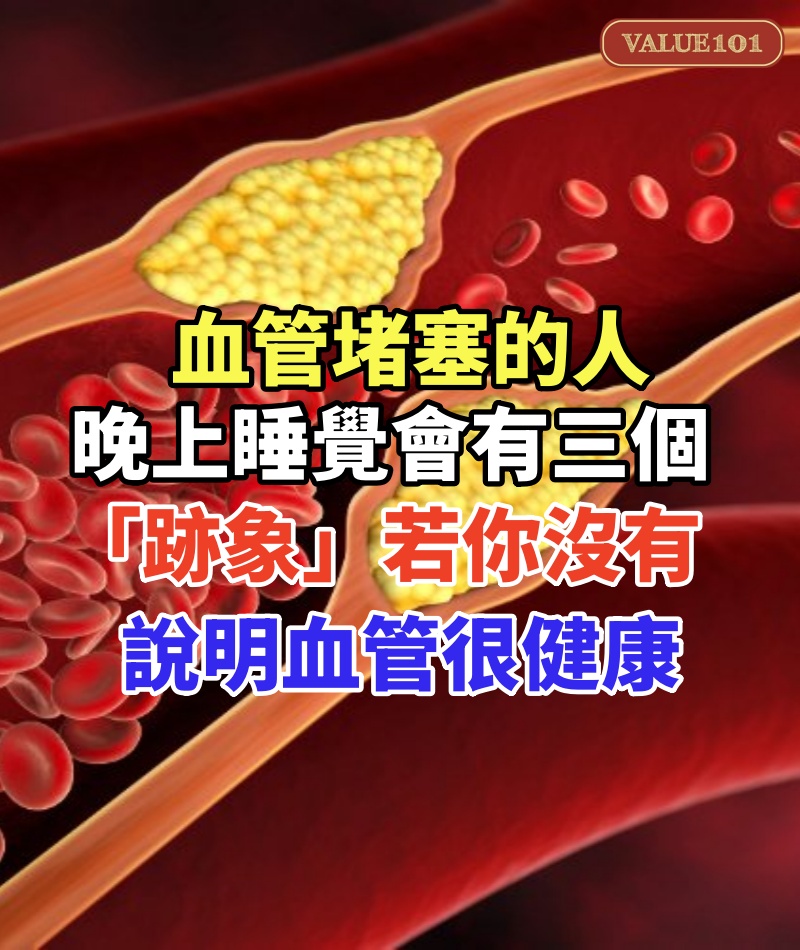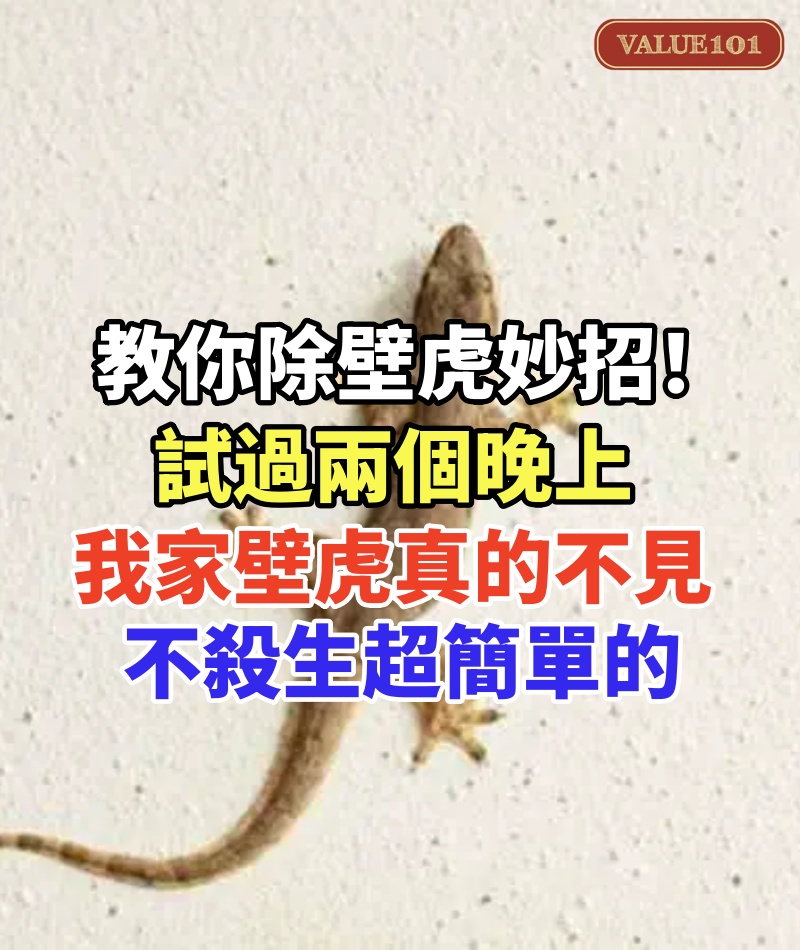40歲以後最節能的活法

他的頂頭上司駱秉章,人品好,有才幹。
結果他對這位上司也「頤指氣使」。
訓練水師,直接給駱秉章說:我一個人就行,你啥也不懂,別來摻和。
派兵求援,也是大爺嘴臉:唇亡齒寒,你不發兵,你也得完蛋,但凡聰明的,也不用我提醒。
駱秉章罵他剛愎自用,態度傲慢。
他反而說駱秉章為人刻薄,不好相處。
就這樣,他把湖南官場得罪了遍,別人對他處處掣肘。
他每日疲於奔命,都來應付這些官場上的手段。
因為始終無法做出成績,最後被奪去兵權,遣返回家。
第二次出山的時候,他已經48歲。
他這才收起了自己的一身刺,懂得了「和光同塵」的道理。
面對比自己官位小得多的縣令,也親自登門拜訪,請人指教。
對待同事同僚,也變得禮貌周到。
曾國藩開始與世界和解。
鮑超愛財,但是打仗英勇,他不再苛責。
手下書生愛名,他也不戳穿,待之以禮。
下屬同僚愛升官,也盡力保舉。
對抗轉為圓融,他開始一點一點被湖南官場接納,也慢慢被朝廷信任。
如此他才得以調動全國之力,平定叛亂,封侯拜相。
莊子在「庖丁解牛」的故事裡說過一句話:官欲止而神欲行。
刀子順著牛的脈絡往前走,才能沒有阻礙,刀身才不會損折。
如果這個人的自我太碩大,總是執著於自己的想法,處處對抗,不是斬到牛骨上,就是卡在縫隙裡,刀身很快就會被折斷。
上善若水。
一個人要像水一樣,包容萬物,不爭不害,才算是真正接近大道。
收斂傲氣,謙卑處下,懂得尊重和寬和,才能保存自身,成就一番事業。

03
王安石早年推行新法。
司馬光等守舊派認為新法太過激進,應當謹慎為好。
王安石卻認為只有自己的新政才能革除積弊,革新吏治。
面對司馬光等人的勸說,一句話也聽不進去,反而指責守舊派愚昧無知。
當著眾多朝臣面,讓他們回去多讀點書。
言下之意:你們都是糊塗蛋,只有我才是對的。
爭吵無果,他就藉著皇帝的助力,他把反對新法的人通通打倒。
貶諦的貶諦,流放的流放。
但後來證明,新法確實太過激進,嚴重擾亂民生。
王安石為新法耗盡一生心血,到頭來,變成了一項禍國殃民的惡政。
在王安石眼裡,只有自己是對的,別人都是錯的。
凡事以自己為中心,總覺得世界處處和他作對,實際上,是自己認知匱乏,胸懷太小。
樊登曾有一個觀點:只有批判性思維,才能減弱自己和世界的摩擦力。
永遠不要認為自己唯一正確。
從多個角度出發,反省自己,批判自己。
這樣才能理解不同,尊重不同,減弱自己和世界的衝突。
東漢有位名士,叫郭泰。
有一次,他和子許、文生兩人到市集逛街。
文生見什麼買什麼,貪婪無度;而子許什麼都不買,過於摳門。
旁人看不下去,問郭泰的看法,郭泰說:“子許少欲,而文生多情。”
只觀察,不評判;只呈現,不議論。
世界是一個萬花筒,存在即合理。
每個人有自己的經驗、三觀、立場,每件事都有自己的歷史、淵源、規律。
把自己當成評判的標準,人生只能處處受限,寸步難行。
學會尊重不同,接納不同,把一切看順眼,人生的路,才能順暢一點。
▽
聽過這樣一句話:
“任何事情,沒有對錯,只有接受與不接受。用智慧改變能改變的事,用胸懷包容不能改變的事。”
很多時候,我們和這個世界的摩擦不是來自外界,而是來自內心。
年輕的時候,喜歡指點江山,與人與事多有摩擦。
看不慣的事多,能量的損耗也重。處處較勁,處處碰壁。
人到中年吃了虧,吃了苦,才明白看人不順眼,很多時候是自己修養不夠。
拓寬自己的視野,放大自己的格局。
學會尊重差異,保持謙遜恬淡,境界高了,一切都順了。
點個讚吧 ,與朋友們共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