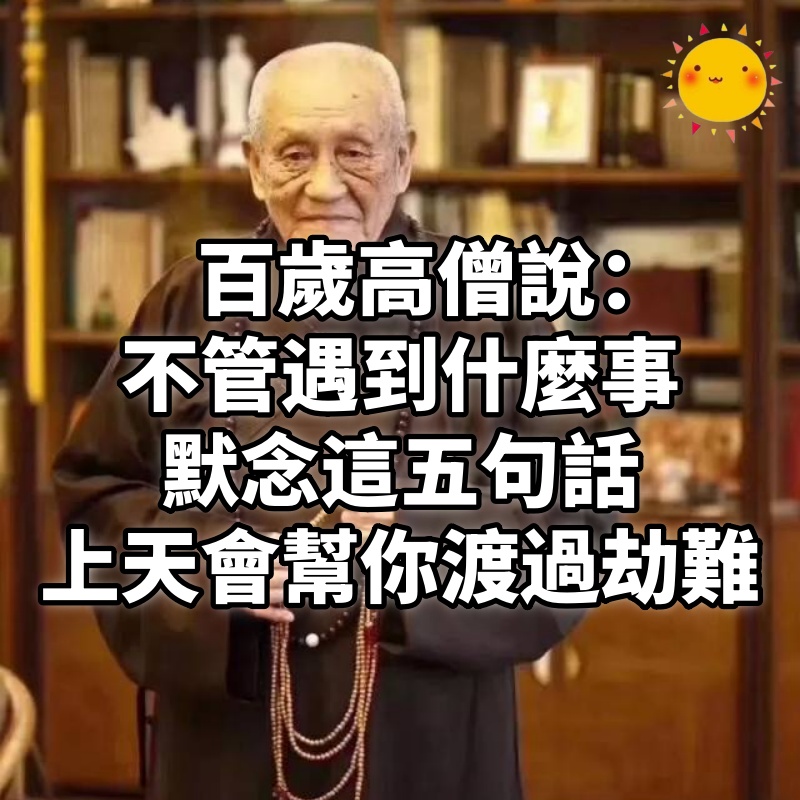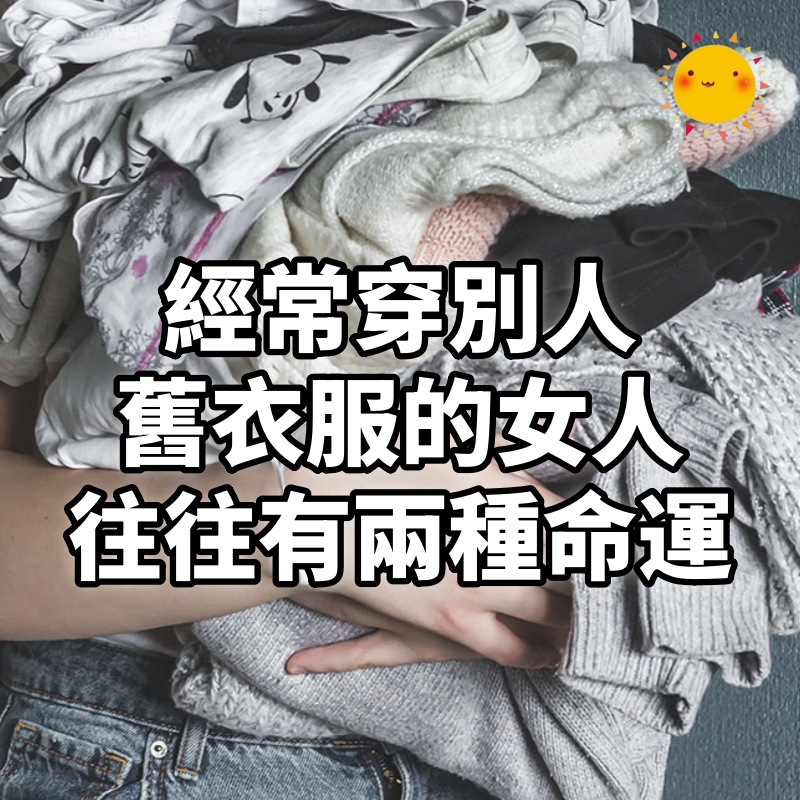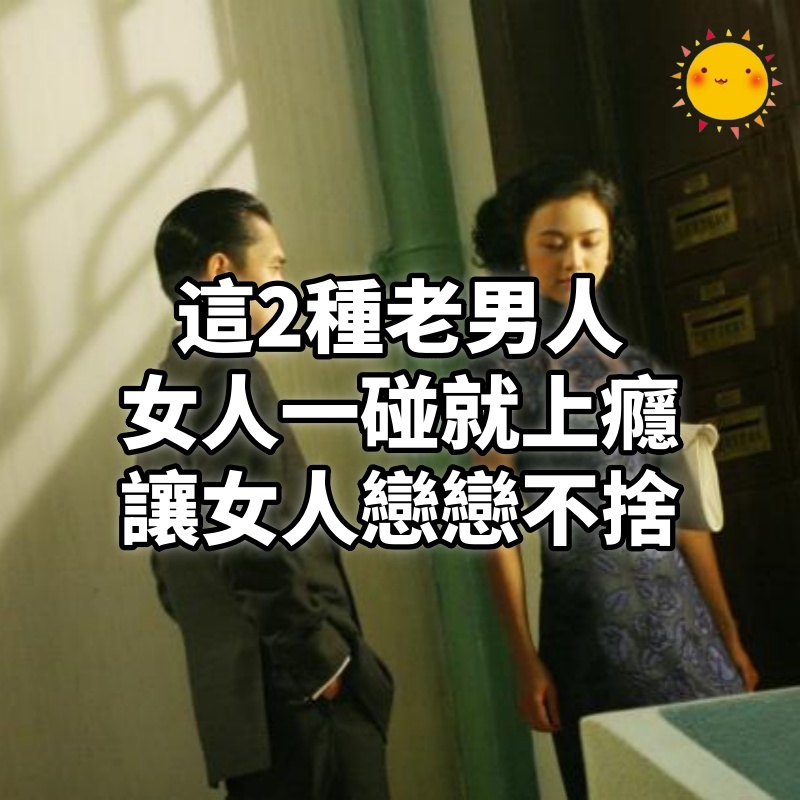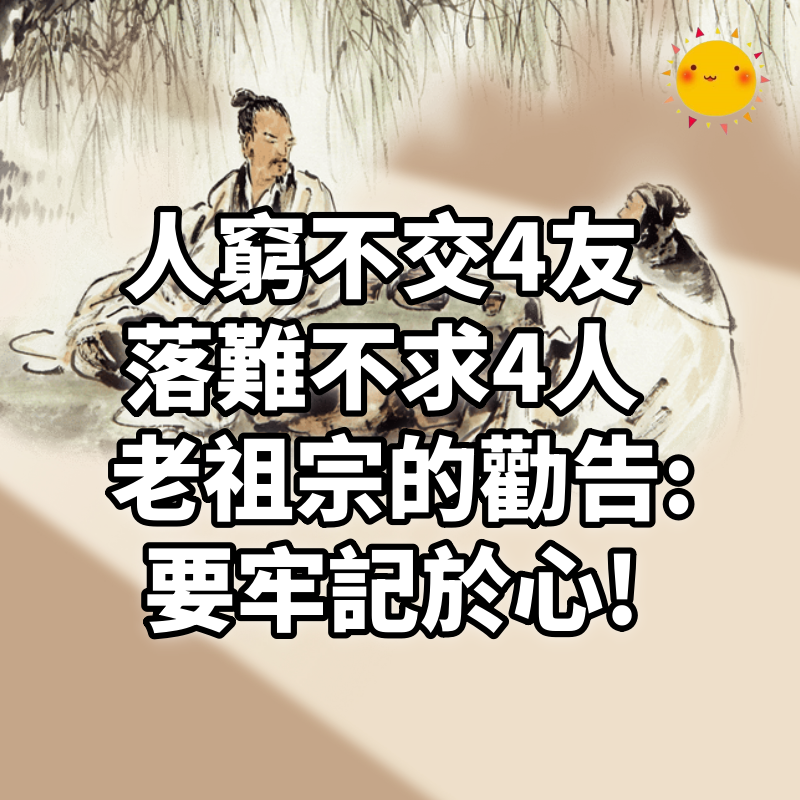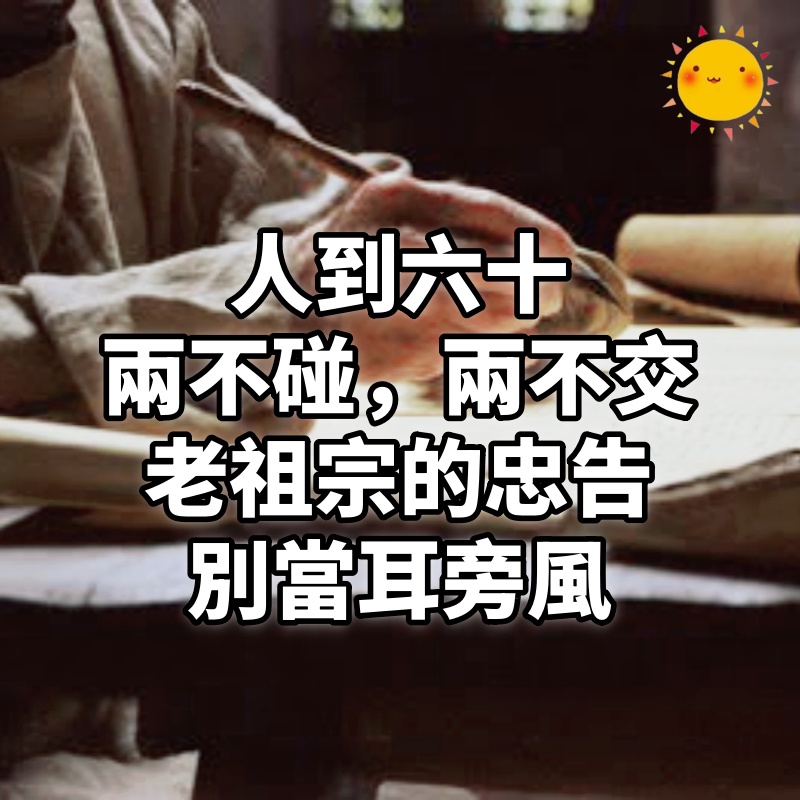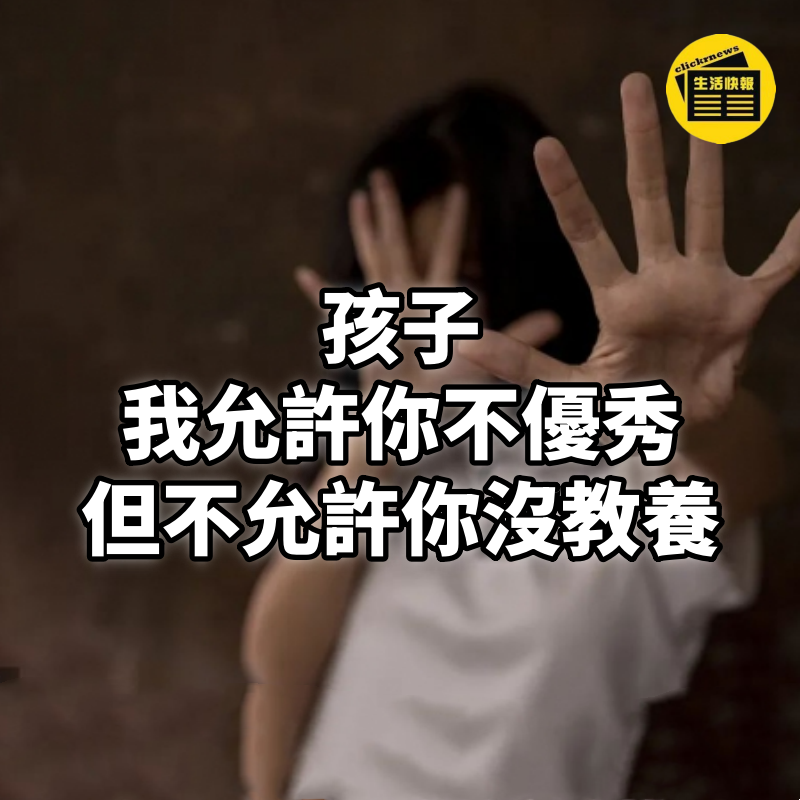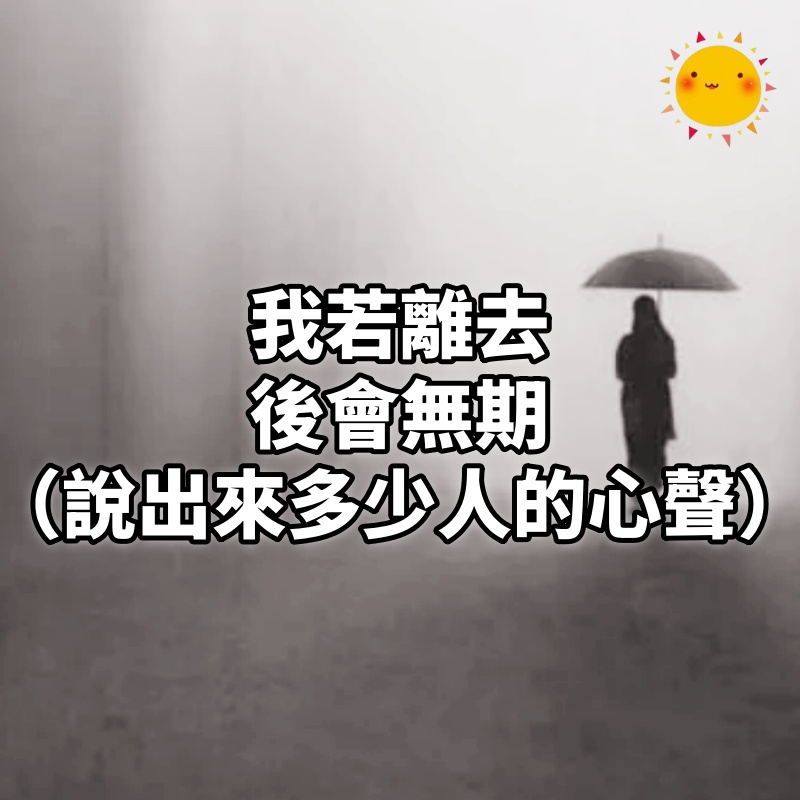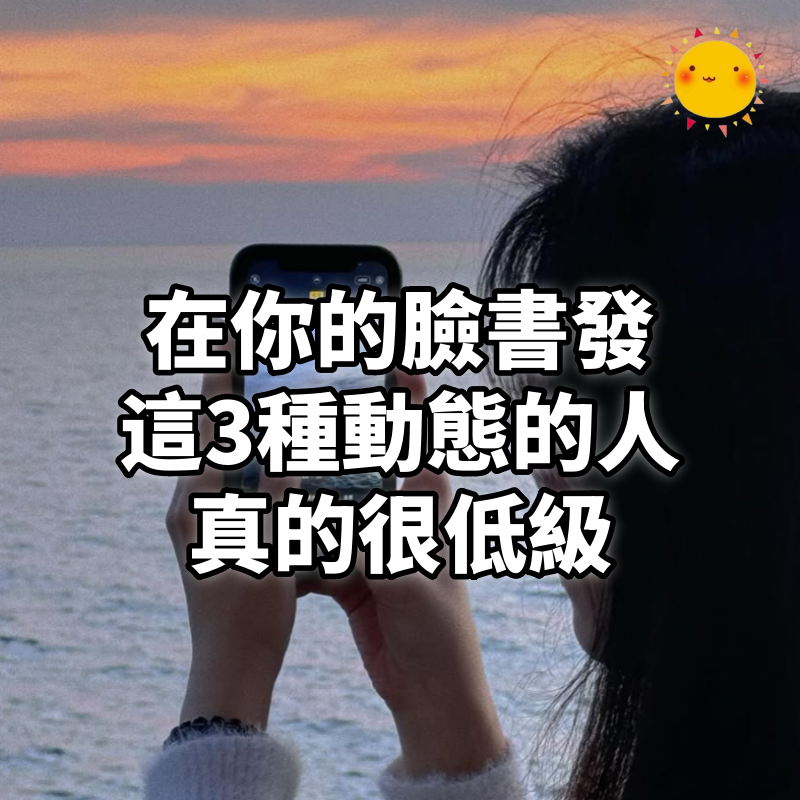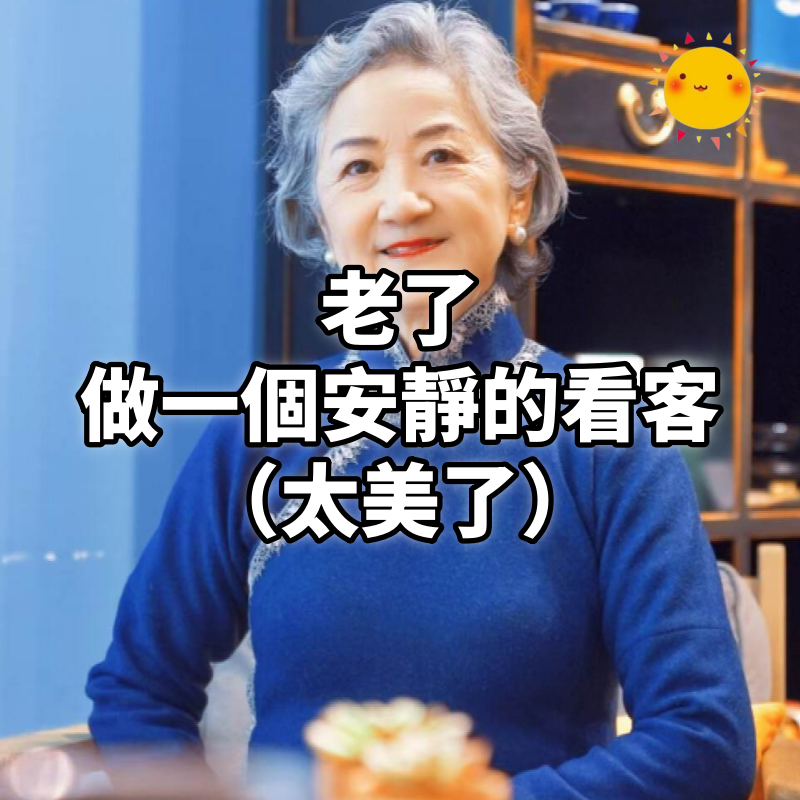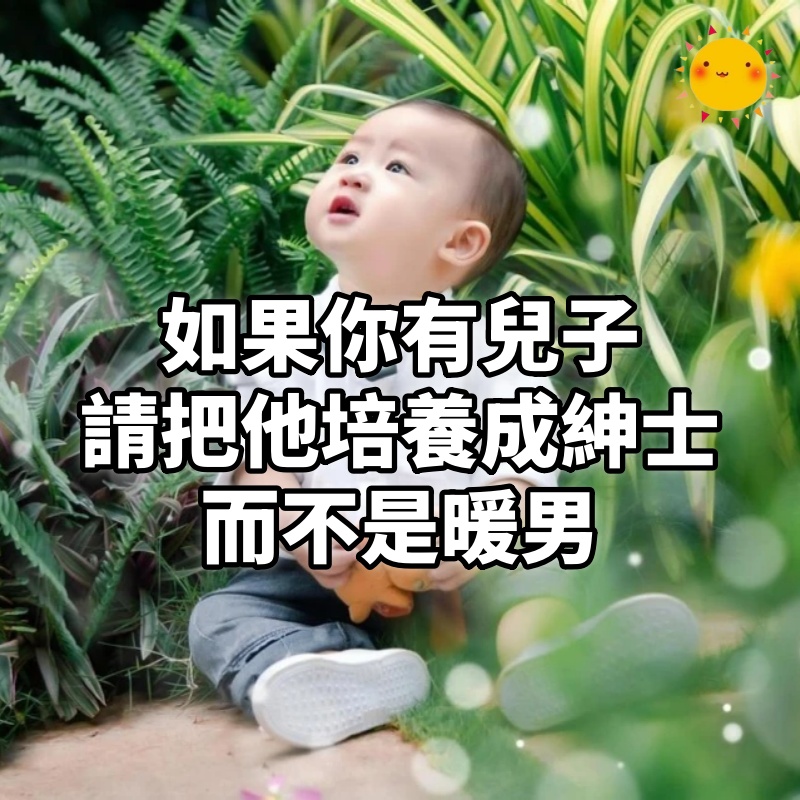「新型不孝」比啃老更可怕!很多父母渾然不知,還逢人就炫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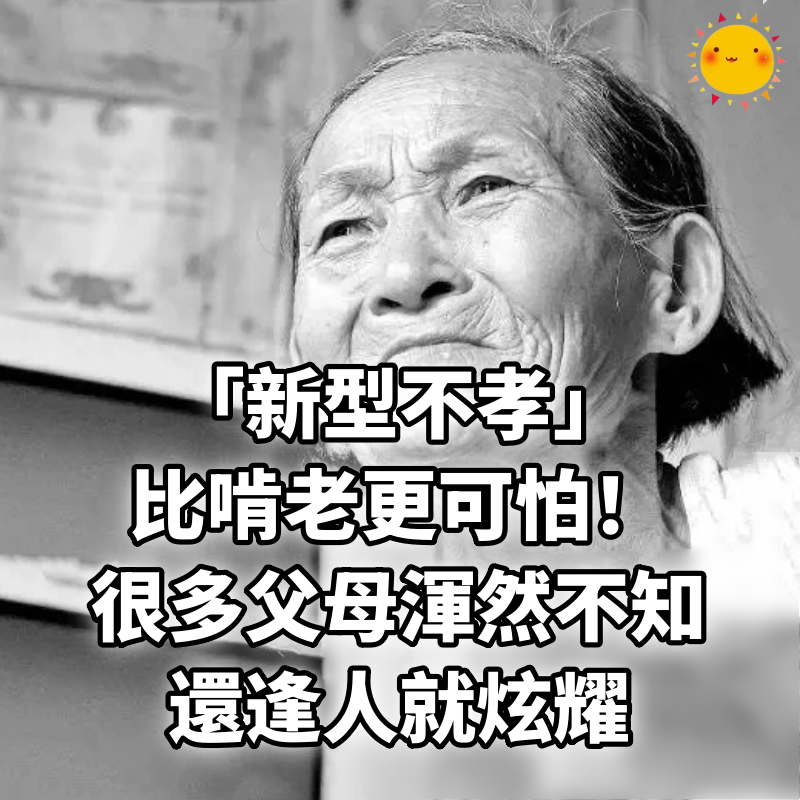
6 / 11
或許他的故事並不特別,但背後映射出的,是一整個時代正在經歷的沉默現實。
當我們在時代的洪流中奔赴更廣闊的天地,留在身後的,不只是老房子和斑駁家俱,還有原地老去的父母與他們日漸緊縮的生活半徑。
在全球化的浪潮中,越來越多的子女離開故鄉,父母卻無法同步「遷徙」。
當物理距離被視訊通話和匯款帳號替代,真正缺席的,是觸手可及的照料與情感的溫度。
這種「空間遷徙」,在過去的時代並不常見。
可在全球化與城市化背景下,越來越多的子女選擇去更遠的地方讀書、工作、定居。
當代中國家庭,正在經歷一種「地理上的裂變」。
老人留在原地,不只是身體上的停留,更是文化、語言、生活習慣上的滯留。
而子女在遠方,不只是地理的轉移,更是時間感知、情緒頻率、生命節奏的錯位。
他們都愛彼此,卻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現實:有些愛,在時差面前變得遲疑,在距離面前變得無力。

7 / 11
高建勛沒說過後悔。
他依然驕傲於女兒們的成就與獨立。
但他也開始習慣用「別擔心」來替代「我其實需要你」,用「我可以」來迴避「我其實撐不住」。
他選擇了留在原地。
但在某種意義上,他留下的,是那代父母對「家庭」的堅守,是對親情不能被搬遷的倔強,是一個老人在全球化浪潮中最後的、微弱的執拗。
在這樣的時代,「高建勛們」的選擇看似「固執」,實則是無聲的抗議——對陌生環境的恐懼,對被「遷移」的生活方式的拒絕。
這不僅是這一個老人面臨的養老困境,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正在面對的「精神贍養困境」,孩子遠在他國,父母老在原鄉,親情在地圖上被拉扯成一條無法拼合的折線。

8 / 11
第三、養兒防老」還成立嗎?
「養兒防老」,是幾千年來鐫刻進骨子裡的共識。
在農業社會,孩子既是勞動力,也是晚年的依靠。
那個年代沒有社保,也沒有養老院,養老幾乎完全依賴家庭內部循環。
養育子女,是一場漫長而樸素的投資:你為他擋風遮雨,他為你老來送終。
可這一套觀念,在高建勛這一代人晚年到來之時,開始鬆動,甚至瓦解。
他曾經也是「養兒防老」的堅定信奉者——否則,也不會在自己最辛苦的中年,把全部資源傾斜給三個女兒,砸鍋賣鐵也要供她們出國。
他想得很簡單,送她們出去是為了她們好,將來她們有出息了,也能回來幫襯他這個老父親一把。
但他沒想到,子女成長的路徑,不再以「回報家庭」為終點。
她們去了更廣闊的世界,有了自己的生活節奏和社會角色。
不是不孝順,而是在新的語境中,「孝順」本身也被重新定義。
它不再意味著陪伴與反哺,而是「理解」「尊重」「問候」和「金錢支持」的組合。

9 / 11
可對高建勛來說,這樣的「孝順」過於抽象。
他要的不是錢,也不是每年固定的禮物或旅遊安排。
他更想要的,是在自己摔倒的時候,有人第一時間來接;是在黃昏散步歸來,有人陪著坐一會兒說說話。
傳統的「養兒防老」,如今陷入了三重困境:
第一,是子女的地理遷徙,打破了家庭的空間結構。
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「就近工作」,而是流向更遠的城市、甚至跨國發展。
歸鄉的路徑,被時間、航班、簽證、生活節奏一一封鎖。
第二,是生活方式的代際差異,逐漸削弱了情感連結。
「爸爸為什麼不告訴我們?」「你們能來嗎?」「你們有時間陪我嗎?」這類問題在父母與子女之間並不陌生,但答案往往彼此錯位。
老人的「需要」在於陪伴,而子女理解的「照顧」則多半是物質層面的安排。
第三,是社會保障的有限替代,無法完全彌補家庭角色的缺失。
當親情無法就位,社會制度卻又尚未建立起充足的承接力——這使得很多老人,在「不能靠家庭、也難靠社會」的雙重真空中獨自老去。
高建勛摔倒那天,他沒有撥打任何一個女兒的電話。
不是不信任,而是他知道,她們回不來。
「養兒防老」這四個字,在很多老人心中依舊閃著溫熱的光。
但現實卻像一道冷水,將它緩緩澆滅。

10 / 11
守望老人,也守望我們自己
高建勛出院那天,自己拄著拐杖辦完手續,回到空蕩的家。
窗簾拉開,春光照進來,陽台上的吊蘭還在慢慢長新芽。
一切如常,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。
這座城市裡,有成千上萬像他一樣的老人,獨自生活、獨自看病、獨自摔倒,也獨自站起來。
他們不是沒有子女,也不是無人問津,只是在時代加速轉動的縫隙中,他們成了最容易被遺忘的那一群人。
我們曾一度寄望於社會制度——養老院、居家服務、社區援助。
但這些仍遠遠跟不上人口老齡化的腳步,服務能力有限、資源分配不均、心理慰藉缺位,仍讓無數老人陷入「生活有人照料,靈魂無人回應」的孤獨。
真正的難題不是老人的摔倒,而是摔倒之後,沒有一雙手,及時伸出來。
當「養兒防老」失靈,社會保障未穩,一個人老去,變成了需要運氣的事情。

11 / 11
那麼,我們究竟該如何面對這一切?
或許,是一通電話的主動問候;是一場視訊里的認真傾聽;是一份備用鑰匙的信任託付;是一場摔倒之後,彼此都知道該怎麼做的默契。
親情不該被距離隔斷,也不該在制度和現實的縫隙中消失。
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牽掛,也是一種需要學習的新能力。
高建勛的故事,不是孤例,而是鏡子。
照見的是當下千千萬萬個家庭,照見的是老去的必然,也照見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——去接住那個遲來的擁抱,和那一場猝不及防的摔倒。